9月17日晚,北京冬奧會吉祥物“冰墩墩”和冬殘奧會吉祥物“雪容融”同步發布。在發布前,記者采訪了北京冬奧會吉祥物設計團隊成員、項目總執行、廣州美術學院視覺藝術設計學院副教授劉平云。
劉平云向記者透露了設計和修改冬奧會吉祥物的過程。據他介紹,設計素材文件就超過了10個G。劉平云說,從盼盼到福娃,是一種傳承,也是一種大國形象的展示。希望“冰墩墩”能在傳承之下有所發揚,有所創新。
攻堅階段一個月瘦了十幾斤
新京報:你是整個項目的總執行。吉祥物核心的創意是冰殼,能否介紹一下靈感來源?
劉平云:我是南方人,江西人,也會偶爾看到雪。讀小學的第一堂課第一篇文章是我愛北京天安門,對天安門有有憧憬、有想象,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來過北京。對北京印象就是冰糖葫蘆,來玩的話都會買一串,作為手信也好,作為當地的特色也好,那對我來說就是北京的感覺、北方的感覺。
我當時做了五個方案,其中一個是就冰糖葫蘆,想著這是我的一個兒時記憶,也是我的一個憧憬。當時只是方案之一,從團隊來講的話,也不會認為它是一個有絕對優勢的設計,只是我們的創意之一。
新京報:設計吉祥物時來了北京多少趟?工作量大嗎?
劉平云:我整理文件,文件已經超過十個G,具體數量還沒統計,可能成千上萬。因為我是總執行和統籌,每次來北京都會把任務和意見全部收集在一起,變成文本。我的文件夾里除了第一次投稿,后面又設了21個文件夾,就是我們21次大的修改節點,小的就更多了。
來往北京廣州一次算一個節點,這樣算的話有21次的交流見面。
我當時在澳門讀博士,有段時間晚上10點澳門那邊上完課,從那邊趕回廣州,到廣州是凌晨12點,一般是在凌晨15分到工作室,指導學生進行一些創作,包括我自己的創作。工作到兩三點鐘再回去休息,上午起來繼續工作一段時間,下午又趕回澳門上課。
這樣大概持續了將近一個月,因為是在攻堅階段,任務很重,很多修改意見需要出來。我瘦了十幾斤,原來140,150斤左右,現在我130斤。
尋找一個“與眾不同”的熊貓
新京報:修改設計中最困難的是什么時候?
劉平云:4月份最難。因為3月初的時候,奧組委給出意見,圍繞珍稀動物去設計。剛開始只是拿著這個意見來做修改,問題不是很大。4月的時候,我們確定做熊貓,并且想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熊貓,這是最難的時候。
我們成立了一個資料組,每天尋找全球畫過的熊貓形象來比對,因為這是一個全球盛會,你一定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熊貓,才有差異化。所以一旦別人畫過的有這個元素的,就不能使用。這個時候尋找一個特別的、有亮點的熊貓,是我們最難的時候。
當時我們有兩個方向,一個偏寫實,一個偏抽象。這兩個點的話,我們在把握上在綜合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。我們想,如果畫寫實可能超越不了功夫熊貓,它畫在最前面了,就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高度。抽象的話可能卡通化一點,但會顯得比較幼稚,會讓人感覺是偏小孩子東西。這是個比較難結合的點,這個時候我們就集中精力去突破這一塊。
到了5月份相對穩定,要參照一些比較精確的方向來進行小細節的修改,不斷做一些小調整。
新京報:整個設計團隊查了多少份熊貓?
劉平云:小文件還沒統計,會議室滿面墻都是我們找到的熊貓類型,還找了老虎、兔子、鹿,全部加在一起一定是上萬張。
新京報:你覺得在熊貓“冰墩墩”的修改過程中,哪一個細節改動最多,或者給你印象最深?
劉平云:尋找亮點。剛剛談到熊貓都長得差不多,怎么才能夠讓別人記住,這是最難的。
4月30日我們來北京現場修改,大概5月1日的時候,奧組委的人一起參加討論,有人說有沒有可能把場館的感覺加進去?比如國家速滑館,我們的設計可不可以把它融進來?雙方討論后決定嘗試一下,效果非常好,跟之前完全不同。那是一個大的突破,我們感覺這個亮點會成為一個比較核心的元素。事實證明它確實做到了,拋棄了之前所有的雷同。
在傳承的同時也有新的發展
新京報:和當年的盼盼,還有2008年的福娃,你覺得有沒有傳承和新的發展?
劉平云:的確從元素本身,熊貓,我認為這是傳承,中國跟熊貓的情感確實特別深。從盼盼到福娃,這是一種傳承,也是一種大國形象的展示。同時我們也在想,1990年亞運會到現在,20多年了,我們可不可以有些突破和新的發現。
2022年是一個未來的世界,2022年冬奧會是未來的一件大事,我們希望在傳承之下有所發揚,有所創新。正因如此我們找到了“冰絲帶”,找到了5G,找到冰殼等等。我們認為在傳承之上我們有了新的發展。
新京報記者 吳為
編輯 陳思
上一篇:守正創新擔使命 凝心聚力譜新篇
下一篇:西安文化旅游產業高速增長 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速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











 6150
6150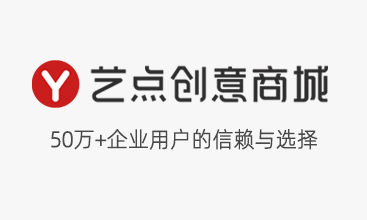


 津公網安備12011102001606
津公網安備12011102001606









